18世纪的中国,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过去人们言及盛世,多把它当作一种历史叙事,侧重历朝的文治武功。这里则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加以探讨,侧重剖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各种支撑因素,以及其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我们将会发现,康乾盛世实际上是由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大要素构成的三重均衡态的表征,但这种均衡态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条件;它在塑就清朝鼎盛时期空前国力的同时,也使其治理形态的演进和财政军事能力的增长趋于停滞,进而对19世纪晚清中国的国家转型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
地缘格局的均衡态
先来看18世纪清代中国地缘均衡态的形成。清朝以前的华夏王朝,远自秦、汉,晚至宋、明,作为农耕民族所建立的以中原为中心地带的汉人政权,对于来自北方和西北部以游牧、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的袭扰和入侵,大部分时间均采取被动的防御姿态,其地缘战略是不对称的。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绵延数千里的长城,成为抵御外来侵袭的最重要设施,大体上也构成了中国北方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界线。能否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直接牵涉到历代汉人王朝的安危。消除“边患”成为其地缘战略的首要任务,也耗竭了这些王朝的大部分财力。
事实上,宋朝和明朝,作为10世纪以来两个最主要的汉人王朝,均因不敌蒙古人或满人的南下而衰落、覆灭。但1644年以后清朝入主中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不均衡的战略格局。自从17世纪50年代清朝完全取代明政权、控制内地各省之后,关内、关外连成一片,长城的军事价值不复存在。清朝的陆地疆域也在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一度稳定下来;其有效控制范围,涵盖以汉人为主体的内地十八省(含1683年收复并隶属福建省的澎湖和台湾),以及入关之前即已掌控的满人部落聚集的东北全境和以察哈尔蒙古人部落为主的漠南蒙古地区。
但清朝在17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地缘战略均衡只是暂时的。康熙年间,不仅内部有三藩之乱,历时8年方才平定,外有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终以1689年双方签约得以解决,而且在此前后迎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即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对外扩张。先有该部首领噶尔丹于1688、1695年率军东进,攻略喀尔喀蒙古,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被清军击败;后有该部首领策旺阿拉布坦于1716年派兵南下,侵入西藏,致清廷于1720年派大军进藏,将其逐出藏区,从此留兵驻扎拉萨。雍正年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于1731、1732年东犯喀尔喀蒙古,先在科布多以西地带击溃清军,后在光显寺反遭清军追击而败逃,随后双方定界游牧,战事暂时平息。乾隆年间,清廷利用准噶尔部上层争夺汗位之机,于1755-1757年先后发兵西征,最终全歼该部,并乘胜击败以大小和卓为首的回部,从此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
经过以上半个多世纪的用兵,清朝的有效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疆域大体稳定下来,其地缘战略格局也在此后出现了历时近一个世纪的均衡态。这里所谓均衡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也是最基本的)含义是,清朝的疆域从1644年入关之后,便涵盖了游牧地带与农耕地带两个部分,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这两个地带之间的不对称战略关系(除了极少数情况下是由中原农耕地带的王朝对游牧地带的部落采取攻势,大部分情况下正好相反);这两个地带之间延续数千年的军事对峙和冲突从此不复存在,从而大大减轻了内地农耕人口为了抵御周边游牧部落入侵所承受的沉重财政负担。但仅仅将游牧地带与农耕地带合二为一,并不意味着清朝的国防安全问题已得到解决。因此,更为重要的是第二层含义,即清朝还必须通过与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反复较量,以及对青海地区和硕特部的战争,一步步建立起对漠北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的统治,不留任何缺口,把周边漫长的非农耕地带(某些研究者所谓“内亚”地区),全部打造成由朝廷直接驻防的边疆,由此建立起牢固的防卫体系。清朝在18世纪中叶基本达到这一战略目标。其地缘安全从此有了全面保障;在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不再存在任何致命威胁。
也正因此,清朝的正规军事建制,包括其兵力规模和武器装备,在18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基本上维持在原有水平,甚至因为长期处于和平状态而走向松弛和衰退。这是清朝地缘格局均衡态的最突出表征。这与早期近代欧洲的列国竞争、相互兼并的状态,以及各国为了生存而全力推动其防卫力量的常规化、正规化,不断更新武器装备,从而经历了一场“军事革命”,适成鲜明对比。
财政构造的均衡态
清朝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主要战略对手准噶尔部,不仅是因为清朝作为原本以狩猎、掳掠和农耕为业的满人所建立起来的政权,本身是在不断的作战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在长期的征战中积累了大量的军事经验和足够的自信;更为重要的是,其军事能力获得了内地所提供的财政支撑。清朝在17世纪后期稳定对内地的统治之后,便在财政构造上逐渐形成一种均衡态,即国库常规年收入与支出均处在大体稳定、长期略有上升的状态,并且在正常状态下总是收入略大于支出,从而产生一定的盈余。作为国库收入最大项的田赋,在整个18世纪,始终固定在每年3,000万两上下。但随着人口增加和商品交易量扩大,包括盐税和关税在内的各种间接税的数额在缓慢上升,清朝国库的总收入从17世纪晚期的3,400万两左右,上升到1720年代每年3,600万两上下。而到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清朝国库的正式收入,每年在4,000万至4,300万两之间浮动,同一时期的国库正式开支,则通常在3,200万至3,600万之间浮动,由此每年产生500万至800万两的盈余。这种盈余最直观的指标,是户部银库的库存,经年累积,其数额在康熙年间最高达4,700多万两(1719年),雍正年间最高达6,200多万两(1730年),而到乾隆年间最高达8,300多万两(1778年),相当于国库岁入总数的近两倍。
18世纪的清朝财政构造之所以呈现上述均衡态,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先看供给侧。清朝常年岁入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最大财源的田赋收入的稳定。而田赋收入之所以稳定,关键在于土地生产率和人口规模都保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从而确保了土地产出在满足现有人口的生计需求之外,还可以产生足够的剩余,使其转化为土地所有者上交给政府的田赋(地丁银);而银价的基本稳定(纳税所需的银两与日常交易所需的铜钱之间保持一个相对稳定、适度的比率)则是确保土地所有者的纳税能力的另一项前提条件。
再看需求侧。清朝常年岁出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边陲安宁,没有重大战事及由此带来的巨额用兵开销。18世纪50年代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这一条件基本得到满足,虽然局部的边陲用兵还时有发生,但其对清朝所构成的战略威胁,已不可与往日的准噶尔部同日而语。二是内地治理的低成本,这在18世纪及19世纪上半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得以满足,因为土地税率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使得清朝国家不必将其行政机构延伸到县级以下,即可以依靠半官半民的保甲组织或其地方变种的运行,完成田赋征收任务;同时,依靠乡绅阶层、地方宗族及其他各种民间组织的合作,也能够维持地方治安。
最后看清廷如何应付重大额外开销。所谓重大额外开销,主要针对两种非常事态,一是国内发生严重自然灾害,为赈济灾民或治理水患,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二是内地或边疆地区发生重大战事,为了平息民乱或边患,需要筹集巨额兵费。幸运的是,康、雍、乾三朝国库拥有巨额盈余,基本上可以应付这些额外开销。事实上,当时的清廷之所以有底气对准噶尔部用兵,正是由于大量盈余的存在,足以支付用兵所产生的开销。清廷做出边陲用兵的决策,往往是在盈余充足之时;每当发生战事,盈余就会急剧下降。战事过后,盈余止跌反弹。待盈余再次上升之后,清廷又会再次对边陲用兵,由此形成若干个清晰可辨的“周期”。因此,户部银库存银成为当时清廷解决边患问题的最主要财政渠道。换言之,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清朝不必通过增加土地税率或其他征税手段,仅仅凭靠自己的财政盈余,辅之以富商的自愿捐输,即可以应付异常情况下的巨大额外开销。
事实上,清廷不仅无须在边陲用兵时增加国内百姓的田赋负担,而且可以在和平年代国库盈余增加而没有适当去处的年份,宣布在全国分批实行田赋蠲免,这跟近代国家形成之前的欧洲各国为筹措财源几乎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截然相反。无论是巨额国库盈余的存在,田赋税额的稳定和低税率,还是康、雍、乾三朝反复实施的田赋蠲免,所反映的都是早期近代以来为世界各国所仅见的清朝财政构造的均衡态。
政治认同的均衡态
最后,还有政治层面的均衡态。清朝以满人政权的身份入主中原后,面临着以往汉人王朝统治中原本土所未曾遭遇的障碍,即汉人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对政权的认同问题。事实上,有清一代,满汉矛盾始终是一个难解的结。清朝入关之初,清廷主要是靠交换的方式取得汉人精英的顺从,最显著的例子是为降清的前明守将吴三桂等人在云贵闽粤一带设立三藩,在所授地域拥有自己的军队和独立的财权、用人权,造成割据一方的局面。这些汉人精英的臣服,因此也是有条件的;一旦其利益受到中央的侵犯,他们便会起而反抗清廷,最终发生“三藩之乱”。
总体来讲,清朝入主中原后,依靠两手巩固其政权。清朝前期,硬的一手用得比较频繁,即以镇压的手段,对付汉人中间出现的一切反满言行。但随着统治的稳定,清廷越来越注重软的一手,致力于弥合满汉之间的分歧和裂痕。事实上,清朝政权从入关之初,即强调其“得天下之正”,把自己定位为继承前明、统治中国的正统政权;内地十八省的治理体系大体上也继承了明朝的架构。与此同时,满人统治精英本身在入关之后便快速汉化,越来越多地接受汉人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在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方面,清朝尊奉儒学,提倡礼教,倡行科举和乡约制度,赢得了绝大多数汉人士绅的认可和忠心。最为重要的是,清朝在国家治理方面,把儒家“仁政”的理念落到了实处,从入关之初,即废除明末的“三饷”,到康熙时期宣布“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前半期,清朝的田赋征收一直处在较低水平,税率大体维持在土地产出的2%-4%,直至清季依然如此,不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同时代的世界各国,均处于最低的行列。
清朝之所以能够长期执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其亟须通过践行儒家的仁政理念,证明其统治的正当和正统;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清朝的地缘战略格局的均衡态,使其军事开支相对于全国经济产出始终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国家有限且稳定的财政需求,再除以庞大的纳税人口,使得清朝在1900年之前的人均纳税负担,一直维持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水平。
除了满汉关系,如何处理好中央与边疆的关系,对清廷稳固其统治地位同样重要。清廷治理边疆的目标与治理内地全然不同。内地对清廷的重要性,在于这些以农耕为主的省份构成了中央财政的几乎全部来源;有效地治理内地各省,也是其统治整个中国、建立起华夏正统王朝地位的根基所在。而边疆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们为清朝统治内地提供了国防安全的保障,而不在于其财政上对中央的贡献。事实上,清廷除了在年班时接受边疆王公贵族们象征性的贡品,对边疆地区在物质上别无所求;边疆对中央没有上交地方税款的义务。相反,中央为了维持边疆驻军及军政人员的开销,不得不在财政上倒贴边疆各地。所有这些,都跟同时代欧亚大陆的其他军事帝国或殖民帝国,把最大化地榨取税款或贡赋,作为其统治所征服地域的最主要目的,构成鲜明对比。正因为清廷的统治对边疆地区并没有带来任何财政负担,也正因为清廷不插手边疆的内部行政事务,同时还因为清朝统治者对边疆的宗教事务扮演了护主的角色,从蒙古到新疆和西藏的广大边疆地区(更不用说作为清朝发祥之地的东北地区),一直接受、服从清廷的统治,极少出现在欧亚大陆其他帝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离心倾向和叛乱现象。相较于18和19世纪欧洲大陆在民族主义激荡下各中小民族为反抗外来统治纷纷揭竿而起,独立建国运动汹涌澎湃,帝国体系四分五裂,清朝18世纪的中原地区和18世纪50年代以后的边疆,总体来讲可谓风平浪静。
三重均衡陷阱
以上所讨论的清朝在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及政治秩序方面所形成的三重均衡态,彼此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地缘格局上的均衡态,亦即清朝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不再存在战略竞争的关系,才有可能出现财政构造上的均衡态,亦即军事开支的有限和稳定性这一主要因素所导致的清朝国库收入与支出水平的相对稳定,且收入略大于支出,产生一定的积余;同时,也正是因为清朝地缘格局和财政构造的均衡态,才有可能产生政治层面的均衡态,使清朝中央有可能在内地实行以低税政策为核心的“仁政”,同时在边疆建立宽松、多元的间接治理体系,维持整个国家的稳定,缔造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长期安宁局面。
然而,三重均衡态在支撑清朝盛世局面的同时,也构成了阻碍其进一步提升国力的陷阱。由于不存在外部竞争,中央没有必要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更没有必要为军队的不断扩充和装备的持续更新而投入巨额开支。因稳定的军事建制和常年军事开支,清朝的财政需求也基本稳定。而内地各省以其庞大的纳税人口,即使在人均税率极低的条件下,也能产生足够的收入,满足其财政需求。因此,清朝国家没有必要为了提高汲取能力而打造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将其行政触角向县级以下进一步延伸;依靠非正式的无须国家财政负担的保甲组织或其变种,地方州县足以完成田赋征收任务,维持社会治安。正因如此,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清朝的军队规模和政府官员人数所占比重,在同时代世界各主要国家中,都是最低的。相对于中国的经济总产值,清朝的军事开支和供养军政官员的开支所占比重,也是同时代世界各主要国家中最低的。然而,清朝国家在享受低成本的治理优势的同时,却丧失了提高国家对内汲取能力和对外竞争能力的动力。
所有这些,跟早期近代欧洲的情形再次形成鲜明对比。16世纪以后欧洲列国竞争的加剧,导致各国为了支撑对外战争以及军事组织和装备的不断扩大、升级,用尽各种手段汲取本国经济资源。以17世纪的法国为例,国王为增加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向金融家借贷,用外包方式征收间接税,以及让贫苦农民承受沉重的直接税(taille)。由此出现国王的债务攀升,政府腐败现象猖獗,国家财政收入损失巨大,乡村抗税事件此起彼伏。总体来讲,在16至18世纪列国竞争的早期近代欧洲,为满足不断攀升的军事开支而提高国家的征税能力,并进一步为此而强化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渗透能力,使官僚机器走向集中化、制度化和科层化,成为国家形成的最根本动力。由此产生的早期近代欧洲各国,往往被称作所谓财政-军事国家。相形之下,18世纪处于清朝“盛世”的中国,由于边疆地区防卫体系的牢固建立和巨额国库盈余的存在,统治者既没有扩大和提升军事能力的必要,也没有加强赋税征收机器的迫切需求。清朝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始终未能提上日程。
均衡态的终结
三重均衡态在18世纪乃至19世纪前半期清代中国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和低水平的。如前所述,地缘格局均衡态的前提条件是清朝国家不存在势均力敌的对手,中国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战略博弈关系。但这一条件并非给定的、绝对的。早在17和18世纪,随着西洋各国航海贸易的扩张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初步形成,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均已经把自己的贸易范围延伸到远东各地,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洋各国传教士的活动足迹,包括他们所传授的先进科学技术。18世纪的清朝统治者对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充满好奇并有选择地加以利用,但对西洋人的宗教和贸易始终怀有戒备之心,最终发展到加以禁止和限制。但是到19世纪上半期,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列强,为了进一步扩张对华贸易,最终还是用坚船利炮敲开了清朝的国门。中英鸦片战争,尤其是中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最终颠覆了地缘战略格局的均衡态;清朝在外来强敌面前节节败退,从此进入“丧权辱国”的时代。
清朝财政构造的均衡态也是有条件的和暂时的。就供给侧而言,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半期,由于两个前提条件的消失,清朝国家的财政供给能力被严重削弱。其一是18世纪后期人口的急剧增长,导致人均耕地面积大幅下降(从1766年每个农夫平均耕种25.22亩降至1812年的14.94亩),人均粮食产量随之下降(每个农夫的产粮总额从1766年的7,037斤下降到1812年的4,286斤),可供汲取的农业剩余也随之减少(粮食剩余,亦即粮食净产值减去用于维持生计的粮食消耗,从1766年的人均439斤降至1812年的120斤)。换言之,农户缴纳田赋的能力也受到影响。其二是由于19世纪前半期鸦片走私贸易的迅速扩大导致白银外流,中国国内市场上白银价格不断攀升,白银与铜钱的比率随之上升,进一步削弱了农户用白银缴纳田赋的能力。在白莲教起义被平定后、鸦片战争爆发前的近40年里,尽管没有重大战事发生,并无巨额用兵开销,但清朝户部银库存银数额并没有如同康雍乾“盛世”时期那样在用兵之后迅速回弹至6,000万乃至8,000万两以上的高位,而在一直在1,700万至3,300万两的低位徘徊,其根本原因即在农业人口的纳税能力大不如前。至于需求侧,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巨额开销及战后对外赔款,导致户部存银降至1842年的1,301万两和次年的993万两,为1686年以来的最低点。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席卷中国南方,控制了作为清朝最重要财源的江南地区。清朝财政入不敷出,其均衡态至此被颠覆。
事实上,太平天国运动所冲击的不仅是清朝财政构造的均衡态,还有统治集团内部权力关系和政治认同层面的均衡态。太平天国公开标榜自己的反满立场,再次撕开了清初以来统治者竭力弥合的满汉裂痕。更为重要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朝的权力重心也在从中央向地方督抚、从满清贵族向汉人官僚转移。以满汉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均衡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即汉人官僚对清廷的无条件忠诚,逐渐转变为“有条件的忠诚”。总之,在19世纪前半期,随着三重均衡态的次第消失,清朝的“盛世”早已成为过去,迎来的将是国运的巨大不确定性,以及晚清政权艰难的转型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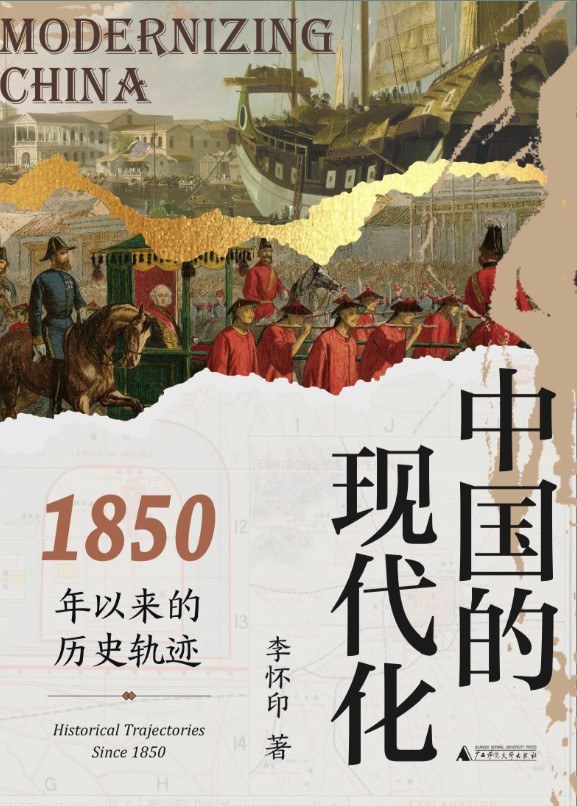
(本文摘自李怀印著《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